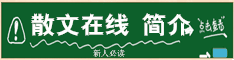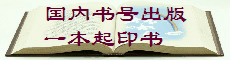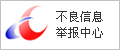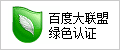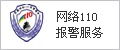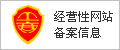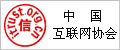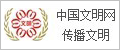|
大堂弟要结婚了,二叔把奶奶安置在他家院子西南角的一间房子里,大门开向他家门口的路。把奶奶原来的土墙老房子扒掉,给堂弟盖了砖瓦新房,也把原来院子的土墙推到,垒了砖墙的院子。从此,奶奶告别了她居住半个多世纪的老院,往那孤单单的一间房子一住,就宣告着她作为那个院子女主人身份的结束。 重盖后的房子又新又大,院子大门也改了朝向,由朝南改为朝向西边的巷子,并装上了气派的大铁门。可是,我不喜欢。可是,不喜欢我也没办法为奶奶争回老院子。 奶奶就在那间孤单单的房子里度过了她最后的时光。那一间房里被简单的家具堆得无处下脚,幸而,可以晒到太阳。冬日午后,奶奶靠在那张磨得发亮的黄褐色的木椅上晒太阳,她会眯缝起双眼想起那半个世纪的点滴么? 老院子有三间堂屋,土墙结构,门两边各有一扇窗户,木窗棱,屋顶覆着麦秸,前后房檐底边用两排青色的瓦片压着。屋子里光线昏暗,散发着霉味和老年人特有的味道。 东边一道不太高的土墙和邻院分开,那边住着我本家的大爷一家。隔着那道土墙两家人可以相互对话,递送东西。墙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豁口,那是我们几个孩子趁着大人不在家时从两边相互爬的结果。因为大爷家是两进院子,若从奶奶家到他家去,要绕行好远。几个孩子约好一起玩,就会翻墙而过。 西边是两间厢房,也是土墙,屋顶铺的却全是青色的瓦片了。我就出生在这两间房子里,不过,对于在这房子里的生活我是没有任何印象的。母亲说,我们搬到后院住时,我还不会走路。但是从我四五岁时,有了弟弟,我晚上又到这个房子里住了。那时,叔叔们都已成家,大姑姑也嫁人了,只有小姑姑住在这西厢房里,我就成了暖脚的。小姑姑爱干净,也把我收拾得利利索索的。虽然那个时候,像我这么大的孩子身上都容易生虱子,我却没有。这是小姑姑的缘故。 和堂屋相对的是两间过底房子,靠东边一间是灶房,西边是进出的过道,大门朝南。灶房里有一个圆墩墩的土灶,灶门口堆着玉米秸或者棉柴棍之类的柴禾,没装烟囱,一烧锅做饭,浓烟滚滚。烟朝上飘,从灶门口飘到屋顶,再沿着漆黑的屋顶从过道两边飘出去。烧火的人坐得板凳矮,闻不到烟。做饭的人弓着腰炒菜也呛不到。从门口进来的人就惨了,会被呛得眼泪直流,赶紧低头跑过。小孩子个子矮,也不容易呛到烟,会来去自如。 灶房里总是最有烟火气,却也是最让人喜欢呆的地方。有一次小叔叔和爷爷在灶房里劈柴禾,居然从碗口粗的干树枝里劈出了几条肥嫩嫩的虫子,爷爷趁着烧火把它们烤的焦黄香酥,全进了我长满馋虫的肚。不过奶奶更偏疼姐姐,因为姐姐从小就跟着她睡,和她格外亲。那一次,我也是从外面进来喊姐姐回家吃饭,正赶上奶奶一边烧火,一边在灶膛里烤着捉来的小麻雀,烤熟的就撕开喂给姐姐吃。看到我进来,奶奶就随口问我吃不吃。看着姐姐吃的满嘴乌黑,心里虽馋,我却不好说吃。因为那时好像已经知道女孩子太馋总归是件不太好的事,就口是心非说不吃,却借口等姐姐一起回家,就那么眼巴巴地瞅着奶奶一块一块地撕给姐姐吃。那个香啊,对于五六岁的我来说该有多大的诱惑!姐姐终于吃完了,奶奶给她擦擦嘴,我们一起回家了,一路上,谁也不说话。 门口左边有一棵一人合抱的泡桐树,泡桐树下有一个石头搥窝子,一个装着木头柄的厚重的石锤放在那个圆圆的石窝里,石窝大约一拃深两拃阔的。姑姑、婶婶、大娘们经常端着玉米、豆子、红辣椒之类的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一边一下一下地挥动石锤,并不时把里面的东西搅拌均匀,一边和旁边邻居们唠着嗑。家长里短,鞋样子、鞋垫子、勾花描图的絮叨着。那些熟悉的声音和容貌就那样不紧不慢地伴着石捶一上一下地飞,飞进了儿时爱听闲话的小丫头的脑海里。到了月明星稀的夏日夜晚,我会坐在搥窝子一边的耳朵上,隔着梧桐树斑驳的树影望月亮。那时视力特好,月亮里边的桂花树和捣药的嫦娥、呆在边上的玉兔都能看到。我甚至还看到一群穿着五彩霓裳的仙女绕着月亮飞过。我每次很高兴地把它告诉大人,他们都只管笑笑,就不再睬我。也许那些是从月亮边飞过的五彩云吧,那在孩子的眼睛里却是多么奇妙,充满幻想。 在往东是一道两米多高三米多长的围墙,墙那边还是大爷家的院子,一棵高大的枣树越过墙头伸出长长的枝条。我清楚的记得小枣熟时,大娘指挥着我们几个孩子在树下铺上塑料纸,大堂哥用竹竿打枣,青中泛红的枣子噼里啪啦落下来,砸在身上生疼生疼的。 往南就是叔叔们家的房子,一排四间,土墙青瓦。后墙靠近屋檐处,隔不多远就会有几个小窝窝。那时,不知那些窝窝做什么用的,倒是经常能在里面捉到小鸟,或者摸到小鸟蛋。因为平车不用时,叔叔们会把平车掀起来,靠在墙上,平车轮子收回家里放着。平车背面是一个一个的木制横档,小孩子踩着这些横档,很轻易地爬了上去,手一掏,就能伸到那些为了修缮房屋搭架子留下的窝窝里,抓到嘴巴黄黄、唧唧直叫的小麻雀。男孩子会把它带到地上,用绳子拴着,能玩个半天。我虽然也皮得很,但只会把它放在手心里,看一阵,再放回去。因为老麻雀回来后会在边上凄厉地叫着,我会赶紧逃下来。 出了大门往右拐就是一个巷子,通向我家和叔叔家,也通向外面任何一条路。 我对奶奶老院子最早的记忆应该就是堂屋东边窗户下的那株硕大的凤仙花。它长得高过了我的头,满枝的花朵诱惑着我尽力踮起脚,伸出小手去揪,也不知揪了多少朵,衣服上、手上都是花渍。正揪得兴起,被干活回家的小姑姑一嗓子断喝,花落了一地,也对那株花记住了一生。爷爷说:揪都揪了,不如再配点叶子包手盖吧。似乎大姑姑那天也回了娘家。我记得大姑姑给姐姐包,小姑姑给我包,包好后,姑姑们的指甲也包了起来。我晃着十指扎满绿叶、失去自由的手,既觉得没法挠痒痒了有些麻烦,又充满着好奇,不知明天早上一觉醒来会有什么魔法出现。 爷爷喜欢坐在堂屋门口的板凳上晒太阳,奶奶坐在屋里靠着门,戴着老花镜,一天到晚缝缝补补的。我如果能安静地在爷爷身边坐下,他就会给我讲故事。他讲到唐僧到西天取经,回来时大风一吹,把经书吹到河里了,捞出来,都湿透了,只好放到石头上晒,却发现少了一卷书,原来被风吹到其他地方去了。所以这经文就不全了。我不知道唐僧是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取经。我不想听了,就嚷嚷着爷爷换个故事讲。于是我听到了记忆中最好听的鲤鱼精的故事: 一个午后,农夫到地里去干活,忽然下起暴雨,地里无处可躲,回家又太远。于是农夫扯了许多玉米叶,找了一些树枝,把玉米叶搭在上面,形成了一个小窝棚。地头前是一个很大的塘,水很深。塘的四周都是高高的玉米田。窝棚就在水塘边上。农夫躲在里头等雨停。夏天的雨来得快走得急。阵雨过后,天上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农夫从窝棚里探出脑袋,伸个懒腰,一扭头望向塘里,立刻嘴巴张开回不去了。他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在河里玩花船,煞是精彩。农夫看得兴起,慢慢起身想看得更清楚些,他轻轻走到窝棚边上,躲在那偷看。这鲤鱼精在花船上舞着一条红绫上下翻飞,根本就没注意到旁边有人。农夫被鲤鱼精的舞姿吸引住,不仅大喝一声:好!却不料惊动了那个美丽的鲤鱼精,她一转身跳入水中,变成一个红色的鲤鱼钻入水底,再也不见。 奶奶是不会说故事的,但是她在边上做针线的时候会给我讲逃荒的事:日本鬼子要进村了,她和住在一个大院的三大娘都穿的破破烂烂的,抓一把锅灰往脸上一抹,就和爷爷躲到西地的麦田里。但还是遇到了日本兵。日本兵叫爷爷摊开手,他再用手摸,看爷爷手上有没有茧子。奶奶说:有茧子就是种地的,他们就不抓。我赶紧问:爷爷手上有没有茧子?奶奶说:庄户人家手上怎么会没茧子呢!我听了才赶紧松一口气。 慢慢的长大一点,在外面玩累了、肚子也饿了饿了就回家,若找不到吃的,我会跑到奶奶堂屋里去找。堂屋木头做的梁头上有个铁钩子,因为怕老鼠偷吃馍,奶奶会把所有的馍和剩菜放到一个竹篮里,盖上一块布,把篮子挂在钩子上。我够不到篮子,就会找个小板凳放在篮子下方,站上去伸长胳膊,用手费力拿起一个大馍,再换回手,把布盖好,并赶紧下来。抬起头看着竹篮子来回晃悠悠的,我每次都有些担心它会掉下来,不过这样的事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一手拿着馍,一手端着板凳,把它放回去。然后我咬着大馍心满意足地出了门,却从不知道奶奶知道馍少了吗?是谁吃的?却从来也没听到奶奶说馍少的事。 老院子一年到头的生活都差不多。热闹的事情倒是记得几处。 记忆中最大的也让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小叔说好了亲事,我那未来的小婶婶在要嫁进来之前的那年春节过后来走亲戚。这是我们老家的习俗,男女双方在结婚前彼此到对方家带着东西去拜年。杀鸡宰鹅、烹鱼剁肉,我的父母和二叔他们都要过来帮忙,还邀请几个本组同辈份的姊妹来陪贵客,凑够一桌八人。一时间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厨房里浓烟滚滚、火苗子一窜老高,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肉香扑鼻。小婶子穿着鲜艳的衣服躲在西厢房里不出来。本族的大娘大婶和邻居们一拨接一拨地过来,都想看看长得啥模样。我和姐姐混迹在人群里,兴奋得不得了,一会听她们讲话,也不知讲些什么,一会偷偷地钻到西厢房里,抬起头看着小婶婶,并用手轻轻拉扯她的新衣服。小婶婶也不说话,只是笑。 可是小婶婶结婚后和小叔却老是吵架。我看到小姑姑从外面进来后,气急败坏地告诉奶奶:三哥他们两人又在吵架。于是,奶奶迈着那双小脚,急匆匆地出去灭火去了。 小叔结婚和小姑出嫁要比春节走亲戚热闹多了,可是,我却只记得热闹,不记得有多好玩。因为外来的人太多,他们不仅挤占了奶奶的老院子,连堂屋、西厢房里都是陌生的脸,我不喜欢他们的霸占,大约我的记忆对这种不喜欢进行了主动筛选,把细节都给抹去了。因为,我更喜欢出嫁后的小姑姑回娘家时的热闹,我觉得那热闹里可以有我的参与,所以我很喜欢,记忆里也把小姑姑回来的场景作了浓笔重彩的雕凿。 春节时,小姑姑和小姑父来给爷爷奶奶拜年是很隆重的事,尤其是婚后第一年,新姑爷上门认亲,讲究的就更多了。我们那姑爷认亲须带着几只活鸡、几条大鲤鱼和一大板子猪肉,外加烟酒、果品,放在盒旗子里用两辆自行车驮过来。那要单请人送的,并且陪着送东西的人必须是擅长喝酒的,否则,这姑爷只怕会被娘家人灌醉不说,还会落下笑柄。 却说小姑父带着人和东西到了奶奶家,那种热闹场景和小婶子来走亲戚类似,但却更热闹。小姑父是主客,要坐主位,也就是八仙桌对着门的上位,其余的客人和家族里请过来陪客的同门同辈的哥哥兄弟分居其他座位。小婶婶那时来吃饭照例要喝酒的,也有劝酒的,但因为是女客,劝也只是象征性地劝,喝也只是象征性地喝。一顿饭吃下来,文雅得很,也拘束得很。男客吃饭就不同了,喝酒那是真喝,劝酒也是真劝。两下来找的陪酒与喝酒的都是真有酒量的,好好的一杯酒不端起来立刻喝掉,而是经过一番唇枪舌剑、义正辞严地劝酒词后才会干掉。双方你来我往,声音一波高过一波,热闹至极,似乎把屋上盖子都掀翻了。小姑父在那盘红烧鲤鱼上来后,把用红包包好的喜钱放在托盘上,由端菜的送给厨师以示谢礼,在桌上大家你来我往喝得面红耳赤时溜出去,到西厢房和小姑姑说话。我会跑到里面一边玩,一边听他们讲话。小姑姑和小姑父讲话很温柔,声音很轻,带着笑。等到他们不讲话了,小姑父转向我,笑吟吟地说:这个小胖丫头是老几呀?我不睬他,只管蹦蹦跳跳的在里面不停地兜圈子。 新婚后的小姑姑平时还是经常回娘家的。她回来后会和奶奶一起做饭。那时正流行大幅的丝巾,方方正正的。新嫁娘都有。也只有新嫁娘才会围着那种鲜艳的丝巾,穿着粉红的褂子。小姑姑那时就穿着粉红色新衣裳,大红色的丝巾不是围在脖子上,而是包住头,往后面一系,长长的垂在脑后,好像飘飘的云。她一边在灶台上炒菜,一边笑吟吟地对着烧火的奶奶娇嗔地抱怨:这丝巾好滑,老是往下掉。我从院子里探着脑袋,往厨房里看和从前不大一样的美丽的姑姑,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小弟弟和堂弟妹们陆续出生了。院子里养了一缸的红鲤鱼,奶奶陆续把它们清炖了,盛了好几碗,却没有我的份。因为弟弟妹妹们在胳膊上种了花,红红的肿得老高。母亲和婶子们各端着一碗,去了刺,小心的喂给各自的孩子吃。我和姐姐只有在边上看的份了,看着那些漂亮的小鲤鱼进了那几个小家伙的肚子,他们还不知好歹得唧唧歪歪地哭,似乎很不乐意吃那些少盐没油难嚼的东西。母亲偶尔会递给我一勺,我坚决不吃,心里却在想着那美丽的鲤鱼精会不会在晚上出现。 姐姐上学了,她会在周末把几个比她小的孩子聚集在奶奶家的过底门口,用那扇破旧的大门做黑板,她做老师,教我们数数和认字。我、东院二大爷和三大爷家的堂妹美芳和红郡以及本族的比我大一岁的两个侄子各自搬个小板凳,把手背在后面,很认真的样子。每次都是我先数到一百,他们几个卡在那数不动,姐姐就会允许我随便玩。我就在一边边玩边看着他们数不下去的样子很着急就会插上去帮他们数。 等到堂弟堂妹那些小家伙们到处跑的时候,奶奶的老院子已被他们霸占,一天到晚叽歪子狼嚎,地上一片狼藉,什么也不能养,什么也不能种了。我也上学去了,只在放学时才偶尔过去。 二婶越来越强悍,仗着是奶奶的亲外甥女,二叔也不管她,里里外外使着横。有一天下午放学,我背着书包,从二叔住的前院门口的路上回家,走到通往奶奶家的巷子时,发现门口围了好多人。往前紧跑几步,忽然发现二婶正一蹦好高的从奶奶家出来,被几个人连拖带拉的往她自己家劝。二婶那张宽阔的脸扭曲着,高高的颧骨往上直顶,想要把脸冲破,脸色红得发黑,薄薄的嘴不干不净的嘟囔着。二叔在后面装腔作势地拿着一只鞋,咬牙切齿地叫到:再骂,捶死你!但并不真的动手。我赶紧跑到奶奶家,一进大门,就发现爷爷坐在灶房的板凳上,正气得发抖。后来才知道脾气温和一直生着病的爷爷不知哪句话惹恼了二婶,令她当场翻脸,不分长幼地发起疯来。二叔当着一大家人面放不下脸来,说了二婶几句,结果那婆娘一蹦三跳,乱骂一气,惹得许多人半拉架半看热闹。 这个窝里横的二婶后来因为琐事和东院的大娘发生争执,却被大堂姐隔着那个破墙头一番子唾沫横飞,声色俱厉地连说带骂,给败下阵来。一向不把家里人放在眼里、处处爱占小便宜的二婶居然让还没出嫁的大堂姐训得流泪。她边哭边对着墙头那边说话,嗓门也不高了。大堂姐却不再理睬她,一扭身进了屋。丢下二婶一个人站在奶奶院子里哭。我那时看不明白二婶为什么怕大爷他们一家。但我知道大爷是村里干部,大娘是不需要上地干活的。 自那次被二婶气伤以后,爷爷病倒了,在床上躺了好长时间才能重新起来,只偶尔到到门口活动活动。他的身体太虚了,咳嗽不停。堂弟妹们小的时候,爷爷还能佝偻着身体,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把其中的一个揽在怀里,带到门口去玩。现在他自己出去走走都很吃力。 过了一个冬天,爷爷好了许多。他那时慢慢搜集了好多废木料,也有一些是从柴禾堆里检出的木棍。在春日的午后,坐在堂屋门口的一个矮凳上,用一把镰刀在棍子的一头刻着什么。爷爷那时已养起了胡子,白胡须随着手的动作一起一伏。他神情专注,刻累了,就歇一会,再接着刻。慢慢的,那些东西就成了形,原来是一条活灵活现的龙。爷爷每天只要吃过饭,就坐下来刻。我觉得爷爷很辛苦,就问他:爷爷,你不累吗?爷爷只答一声:不累。眼睛盯着龙头,手也不停下来。慢慢的,十几根材料不同、粗细也不一样的拐杖都刻好了。每一条上面都有一条虬龙攀附,摇首摆尾,形态各异,眼睛仿佛活地一般瞪着我。 我把它们宝贝般贴在脸上,学着老人拄着拐走几步路,却不在嘻嘻哈哈地拿它们杂耍了。隐隐的,我知道自己很佩服爷爷:我要是也像爷爷这么手巧多好! 爷爷原来身体略好的时候,每年冬天,他都会用洗净晒好的麦秸秆编圆柱状的馍囤子和圆台样的馍筐子,除了给我们几家用,还帮邻居亲戚做。奶奶纺线坐得小圆团子也是爷爷编的。那时接新娘子,车里放的给新娘做的都是圆团子。爷爷帮别人不知编了多少。西厢房里堆得一堆白里带着黄的秸秆,爷爷就在那队秸秆边上坐着编。他不急不躁,似乎很享受那种生活。我喜欢坐在边上,不说话,一边帮爷爷递秸秆,一边看他那双粗糙的大手一手扶筐,一手抓住秸秆条,灵动地上下翻飞,馍筐随之一圈圈地长高。 入冬前西厢房里还会放很多芦花,有奶奶买的,也有母亲和婶子们买的。爷爷会根据每个人脚的大小给我们用芦花编毛窝子。毛窝子要用木头底,一前一后两个跟。在木头底的四周均匀打上孔,穿上绳子,用芦花一圈圈地编,最后编成一双芦花鞋。鞋里面垫上棉花,甚至打碎的的麦秸秆,到冬天大雪纷飞时,穿在脚上出门,暖暖和和的,不怕冷,鞋底高,也不怕湿。那时棉鞋只有布底鞋,一遇雨雪,鞋底容易浸透水,穿在脚上一点暖和气也没有。穿毛窝子的好处就出来了。那时的冬天也特别冷。雨雪天过后,房屋前后的瓦沿上挂满了长长的冰柱子,小孩子踮起脚,手一伸就能够到。用小棍子一敲,冰柱掉在地上四分五裂成一个个冰晶。有的孩子会从瓦沿上掰一个,放在嘴里嘎吱嘎吱地嚼,像吃冰棍一样。在这样寒冷的冬季,路面会被冻得生硬,毛窝子的木底呱嗒呱嗒打击路面是再熟悉不过的的声音。一家老老小小二三十口人的毛窝子都是爷爷在西厢房里一下一下编出来的。 可是,爷爷再也不能做他爱做的活了。 那是个收麦的季节,我和姐姐在我家和表姐一起收装晒干的麦子,父母都去了前院奶奶家。我小小的心似乎有种预感。前段时间,父亲坐在爷爷床上,把爷爷抱在怀里帮他祛痰,叔叔大爷们围了一屋子,还有那个以前给我打过针的邓医生进进出出的忙活着。我很想和爷爷讲句话,却没有机会。现在爷爷会怎么样了啊?前院忽然哭声一片,表姐说:你爷爷死了。我不吱声,也不哭。过一会,我悄悄地来到前院,穿过人群,来到屋子里,看到父母叔叔们正在大哭,小叔看到我,抓住我的手,哭道:你再也见不到爷爷了。我嚎啕大哭。 此后的冬天我们再也穿不到爷爷编做的毛窝子了,蛮横的二婶也别再指望爷爷为他们家做馍囤子了。小叔后来努力学做毛窝子,可是他太笨,编出来的又泡又丑,一点也不紧致。后来好歹好一点了,怎么也没法和爷爷编出来的秀气可爱合脚的毛窝子比。可是我们也没得选择,只好凑合着穿,毕竟有得穿就不错了。 爷爷刻的那些漂亮的龙头拐杖呢?只有我喜欢看爷爷刻,也只有我想着问。奶奶却道:我一生气,把它们都烧了。为什么生气?为什么烧?我满心地想知道为什么,竟没有问。那时,我在读小学四年级。从此,我知道了见不到亲人的感觉。从此,我有了一个人的哀伤。我在梦里见到了爷爷,他看着自己粗糙却又灵活的的手,想摸我的头,却无奈地说:爷爷不能再摸你了。 没有了爷爷的老院显得那么孤单、冷清。姐姐后来又搬了进去陪伴奶奶。我慢慢长大了,离家越来越远。每次回去,我都会过去看看越来越老的奶奶。也看看日渐颓败的那所老院子。不管它有多颓败,只要奶奶还在那儿住,过往的一切就都还没远去,奶奶依旧是院子的主人。 可是最终它被夷为平地,倒在时光的隧道里,无声地宣告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落在了岁月的尘埃里。那些出生和离去,那些欢声和笑语,那些哭泣与哀伤,那些梦幻与温馨,都像树叶般飘落,飘在冰冷的大地上,化为尘土,成为记忆。 2014、10、29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