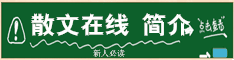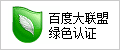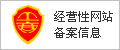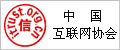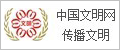|
这地方叫白沙街,名副其实!土壤沙质,又白又细;居民房舍沿街而筑,形成了一条颇具规模的长长街道——五里长街哎。分白南白北两个大队,各自下设十几个生产小队。农田全属公家所有,这公家就是生产队。对长家门口的大树上吊着大钟,不巧,没有大树的,就在门口筑个木头架子来挂钟。这样队长敲钟就十分方便了。每天至少有三次钟声大作:早上天麻麻亮的时候、早饭后以及午饭后,震耳发聩,你说你没听到,瞎说!糊弄谁呢?大家一起出工,一起下工,一起劳动,谁也别想偷懒占便宜,而谁也不吃亏。大家心理都平衡。然而,常常是一天当中钟声不止响三次,有四次、五次的,甚至更多。因为,那时会议特别多,政治学习——上级经常下达一些重要文件,革命群众就要认真学习、聆听,以看清形势,认准方向;开批斗会——抓革命,促生产,防止一小撮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搞各种名堂的破坏。一天的辛苦劳作,到了晚上,没有谁的身体不像散了架一样,粗茶淡饭草草用过后,就想早早歇息,可是,突然要命的钟声响起。有时,大冬天的,刚脱了衣服进了被窝,钟声敲响——钟声就是命令!你不去?你想怎么着?要反党反革命不成?于是,拖着疲惫不堪的沉重身躯,昏昏欲睡,磕头绊脚,迫不得已地向队长门口晃晃悠悠而去。 反正,大人们就是个忙!一天到晚地穷忙乎,焦头烂额,哪有时间与精力顾及其他?顾及孩子们?可是,忙来忙去,一年四季忙到头,却是两手空空,捉襟见肘,缺吃少穿。于是,身心皆疲,没有希望,没有乐趣,日月苦苦地熬着、耗着,就如在无边的苦海中挣扎沉浮。——大人们就更没有心思打理孩子们了。 孩子们完全是放养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天大地大。虽然破衣烂衫,虽然瘦弱苍白,严重的营养不良,但是却快乐无比,就像荒地的野草生长得恣意妄为,欣欣向荣又欢欣鼓舞。十八不跟二十玩,半大不小的孩子成群结队,鱼一群,虾一窝的,在街筒子里来来去去,呼呼啸啸。他们的玩法异彩纷呈,花样繁多,捉迷藏、做游戏都是再普通不过的玩法了,不过瘾,他们就演戏,轮流扮成敌我双方,打街仗。他们还学着大人的样开批斗会,可是没人愿意扮演黑五类,怎么办呢?抓阄,大家都没意见。斗地主,斗富农,斗反革命,斗坏分子,斗老右,真是其乐无穷!当你问他们可有什么玩具?他们会把眼睛睁得圆溜溜的盯着你反问:“嘛玩意?干啥子用的?”一脸的困惑。他们没有任何玩具,甚至没有听说过玩具,却玩得丝毫都不缺憾。有月光的晚上,街筒子里往往要喧闹到半夜,孩子们大呼小叫,欢声笑语如潮水涌动,狗狗们不知所以然,也跟着瞎起哄,一声声狺狺吠叫,茫然而空洞,却响彻夜空。若不是哪个大人心烦气躁无法入眠而出来厉声吆喝,孩子们还会一直闹腾下去的。他们每每就是这样,一玩起来就不亦乐乎,就忘了时间。 不过,白北大队的孩子比白南大队的孩子更快乐,因为白北大队有个大头安,对于白北大队的孩子们来说,大头安就是个天然的超级好玩的玩意儿。 大头安那时候已经成年,有十六七岁了吧,但是,智商却像个三岁娃娃。大家都说他是个傻子。他有名字,叫李平安,但是,每人叫,大家张口闭口就是“大头安”。这绰号来自他那天然的外形特征。他的身胚很壮硕,款款厚厚的,一般成年人的身高,但是,上身过长,两条腿极其粗短,严重的比例失调。且脑袋奇大,有人形容说“像只五升的斗子似的”——就是“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的“斗”。当然,这说法夸张了,就跟说“燕山雪花大如席”一样,那脑袋就是个大,那大脑袋仿佛是直接嵌在了颈窝里,脖颈根本看不出。于是,人们就叫他大头安了。他走起路来更是一景:两条小短腿忙不迭地倒腾着,艰辛地搬运着显得沉重的上身,你会想到一辆严重超载的货车,货物高高堆摞起来,给人一种头重脚轻,摇摇欲坠的感觉。他就像一只笨拙的大黑熊!他说话也是滑稽可笑的,两片厚厚的嘴唇忙碌地翻来翻去,半天翻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语,嘴里好像含着一条无法自如伸曲的大舌头,好不容易送出来一句话,瓮声瓮气,鼻音囔囔,含混不清。看他那样子,你早已忍俊不禁了。 大头安没有父亲,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病逝了,他也没有兄弟姊妹,他母亲带着他,孤儿寡母度日月。他的母亲是个低矮孱弱的小老太婆,缠着小脚,头发绾在脑后,用黑色网罩网成一个圆圆的髻,肥肥的黑裤子扎着裤腿儿,上身儿,热天是白色粗布偏襟褂子,冷天是黑色的。常见她掮着一件什么农具——铁锨、锄头、三齿钉耙什么的,或者手里拿着镰刀,臂弯里㧟着篮子,颤颤巍巍地默默走在上工的路上;黄昏里,下工了,她又悄无声息地沿街走回家去。从没见她笑过,哪怕是一丝一缕的笑影呢,她那黑黄干滞的脸上总是挂着一层化不开的浓厚的凄苦与忧伤。她的步态虽然略显摇晃,但是,她的步履不疾不徐,腰板是挺直的,头是昂着的,目光直视着远处的什么。——现在想来,她的内心应该是强大的吧。也许,只是无奈地苦熬着日月罢了,即便如此,我觉得,她也是令世人敬佩的。唯一的儿子还是一个傻子,她的生活会有什么期盼与指望呢?在那样的岁月里,任谁的心不会像灰烬一样凉呢?可她还在一天一天地过着看不到丁点希望的日子,韧韧地走在上工下工的路上...... 有时,她的身后跟着大头安,大头安带着一件跟她的一模一样的农具。大头安一出现在街头,街道里立即汹涌起一波又一波快乐的浪涛。有一只编排大头安的顺口溜一直唱响在我儿时的村落,也响彻在我的童年里,——“大头安,辘轳脆,他娘打他,他不睡......”——“脆”是我按照发音比葫芦画瓢写出来的。辘轳在当时的乡村是司空见惯的物什,水井两三丈深,辘轳汲水,发出呼噜噜的声音,并夹杂着吱纽吱纽的响声,听起来根本不“脆”。我想,大家之所以那样说只是顺嘴出溜押韵罢了,达到打趣大头安的目的,而自身从中得到无法言说的乐趣。这童谣的创始者是谁,没有那个孩子说得清,反正你说、他说、大家说,就那样在孩子们中间流传开来了,就像当今的流行歌曲在青少年当中流行那样,有事没事,他们都会扯起喉咙嘹亮地喊上那么两嗓子。就连呀呀学语的娃娃也跟着胡乱嚷嚷,那滑稽的样子挺逗的:眼睛挣得圆溜溜的,流着哈喇子,口舌还不怎么利索,哇哇啦啦地直嚷,傻呼呼的!大头安平时不怎么出现在街上,大头安跟着他的母亲下工回来了,走在大街上,这比耍猴的都更吸引孩子们的目光,不管当时他们正在疯玩着什么,都会立马停下来,目光一下子都聚集到大头安身上,那眼睛像灯泡一样,贼亮,忽闪忽闪的,他们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嘻嘻哈哈地说笑。在这样的众目睽睽之下,大头安的母亲看不出跟平时有什么两样,她依然目不斜视,不言不语,从容淡定地走自己的路。大头安会缩缩地,紧走几步,跟上母亲,像是要寻求母亲的保护似的。他们终于走到了自家的门口,那个临街的窄怯的门脸,隐入其后。突然,不知是那个坏小子猛然醒悟似地大声吆喝道:“大头安,辘轳脆,......”于是,半条街像放鞭炮一样噼噼啪啪地响起了这只算不上歌谣的顺口溜,一声声此起彼伏,咕咕呱呱,让人想起夏日傍晚的一池蛤蟆,热热闹闹,如火如荼地叫着夏天。渐渐地他们的步调一致起来,出现了节律:“大头安——辘轳脆——他娘打他——他不睡——”就像打夯的人们喊叫的劳动号子那样整齐划一。他们仰着脸对着天空喊叫,忘乎所以,悠哉游哉,没完没了,宣泄着自己的快乐,乐此不疲......直到哪一个孩子的家长,忍无可忍,凶神恶煞般地跨出家门,一声棒喝:“喊什么喊!你们的娘才揍你们呢!都滚回家吃饭去!看屁股挨揍!”大家伙像兜头泼了一盆冷水,禁若寒蝉,悻悻然各自散去。诸如此类的笑闹经常这样收场。那天傍晚,那洪水一般的叫喊,大头安跟他的母亲不会没听到,但是,他们始终没有露面,吃晚饭时,一向习惯坐在他们家大门的门槛上端着海碗吃饭的大头安也没有再出来。 大头安知道那歌谣是笑虐自己的,不好,很不愿意,有时,气恼了,就回嘴反驳:“你,辘轳脆,你娘打你,你不睡。” 被反驳者就瞪了眼,佯怒,呵斥道:“你再敢说!”并举起巴掌作势要打。 这个时候,大头安就赶紧禁声,低眉顺眼。再不然,扭头逃回家去。大家就哈哈笑说:“其实,大头安可精啦!” 那次激烈笑闹之后的第二天傍晚,大头安就跟往常一样坐在他们家的大门槛上吃晚饭了,不一会儿,大家伙儿也都端着饭碗热热闹闹地聚拢来了。 有人说:“大头安,咱俩换换饭吃吧,我的饭好吃。” 大头安出乎意料的不搭理人,就像没听见似的,搁以往他是有问必答的。那人狐疑,提高了嗓门:“大头安,跟你说话呢!你是聋了还是哑了?” 大头安从碗边抬起头来,咽下一口饭,深呼吸,憋足了劲,郑重宣布说:“别叫我大头安!俺娘说了,我不叫大头安,我叫李平安。恁随便说‘大头安,辘轳脆’,那不是说我嘞,我不管了。” 可把大家给笑翻了,哗哗啦啦的,就像疾风中的杨树——鬼拍手。有人笑得一只手捂着肚子,蹲在地上,连声说:“笑死我了,笑死我了。”大头安看大家笑,也跟着笑——“嘿嘿嘿”,是那样的天真无邪,纯净,明朗,不设防,就跟婴儿的笑一样。 那人故作诧异地说:“你咋会叫李平安?”指着一个叫张虎的孩子说:“他叫李平安。” 大头安有点生气地说:“我叫李平安!他是张虎。” 大家又是一阵笑。 有人就改口了:“李平安,咱俩换饭吃吧?” 大头安,眼睛忽忽闪闪地盯着他的饭碗思忖:“不换!我的碗大,你的碗小,吃亏!” 大家又笑。 “李平安,你吃了几碗饭?” “八碗。” “胡说!不识数。你这才是第一碗。” “八碗!”大头安坚持,毫不含糊,并持之不渝。 有人问:“李平安,你几岁了?” “八岁。” “瞎说!十七了!” “八岁!”大头安瞪着眼睛,梗着脖子,坚持自己的观点。 大家就叽叽嘎嘎地再次大笑。 大头安似乎特别喜欢“八”这个数字,无论谁问他什么有关数目的问题,他总回答“八”。“八”这个音节,在他简单的意识里不知跟什么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大人们猜想说,他是八月初八生的,因为,在他生日那天,他的母亲总是给他煮个鸡蛋吃,所以他认准了“八”就是“好”。——“他精着呢!”大人们都说。那年月里,在孩子们的眼中,鸡蛋可是无与伦比的美味啊。 大头安就是这般可爱可逗。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村子里放映了,孩子们都被深深吸引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该电影还都挂在嘴边,津津乐道。其中一个情景给大家、给大头安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悟空为了保护师兄,从耳朵上拔下金箍棒,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圈住师兄三人。结果,白骨精一靠近,那圆圈就会“轰”地一声爆响,火光灼灼,白骨精吓得一下子就跳开了。有调皮的孩子就在地上随便拾个什么玩意儿——瓦片、石头蛋儿或者破柴烂棍,在地上画一个圈,把大头安圈进去,大头安往往吓得哇哇乱叫,动都不敢动,除非你用脚把那圈儿擦抹掉,否则,他决不敢越雷池半步。 其实,这些孩子们也并不怎么坏,对大头安也只是这些小打小闹的戏谑调侃,没有什么太过分的。实际上,他们打心眼里喜欢着大头安,都愿意大头安和他们一起玩耍。在那单调、苦涩、贫乏的年月里,娱乐活动极度缺乏,大家看一场电影就跟过年一样的高兴,小村落贫瘠沉闷的生活就像一潭死水,而大头安恰似一股别样的清风,死水因之泛出了一缕缕活泼又柔和的涟漪,不至于完全地死寂、僵化。要不然的话,生活还有什么过头儿呢? 女孩子们跳大绳的时候,都喜欢大头安悠绳子,都说大头安悠得最好,均匀,不紧不慢,不轻不重,节奏分明。大头安也很高兴做这样的事儿,尤其得到了表扬后,悠得就更起劲了。 捉迷藏时,大头安就当“老家”,大头安可高兴了,他气定神闲、胸有成竹地坐在那儿,那款头儿,那架势,就像一个将军。他展开熊掌一样的大手,其他孩子们伸出食指,放在他的手心,然后他大声喊道:“豇豆绿豆,咔吧一溜”,随着这声喊,他猛然地抓握,被抓住手指的,要自认倒霉,做小鬼,其他孩子们都去藏,他来捉。捉住一个,下一轮就由这个倒霉蛋儿来做小鬼。大家都不乐意做小鬼。小鬼蹲在大头安的前面,大头安用两手捂着小鬼的眼睛,待其他的孩子们都藏好后,大头安会把嗓门提高到最大,吆喝道:“开——鬼!”小鬼去捉人,有的孩子就会趁机成功地返回到“老家”身边。大头安激动、紧张、兴奋、担心,而往往不知所以然,哇哇哇地乱叫。很不幸,小鬼一个替死鬼都没捉到,只好再做小鬼,颓丧又无奈。 在玩“批斗黑五类”的游戏时,孩子王王帅兵总让大头安当光荣的革命群众,而他本人跟其他的孩子都抓阄,凭运气定身份。王帅兵有几次抓的都是“地主”,他二话不说,每次都高高兴兴地扮演。他们好像都在有意无意地袒护、优待大头安。这不仅仅是因为大头安家是贫农,大头安根正苗红吧。 有一件事很值得一说。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太阳还在西天红彤彤着一张脸,大人们都正在田野里挥汗如雨,这街道遂就成了孩子们的天下。王帅兵领着大伙儿打街仗,他们分成了敌我双方,当然,并非真打,只是玩。他们大呼小叫,呜呜泱泱,疯啊、闹啊、乐啊,像一群出笼的小老虎,无拘无束,无法无天。这样的游戏,大头安是不便参与的,他跑不快,容易被捉俘虏。王帅兵就安排他做观众。此时,他坐在他们家的门槛上,伸着脖子,大睁着眼,半张着嘴,津津有味地观赏,时不时发出他那特有的“嘿嘿嘿”粗嘎的笑声。这时,忽然从南边走来一群跟他们年龄相仿的孩子,估摸有七八个。他们要干什么?在大家狐疑愣神的当儿,只听那群孩子嘻嘻哈哈,十分放肆地纷纷叫嚣:“大头安,辘轳脆,他娘打他,他不睡......”原来是白南大队的一群混小子。对于大头安他们早有耳闻,据说特逗,特搞笑,还怪模怪样的,跟个天外来客一样。他们来者不善,是要一探究竟看热闹的。这怎么行呢?“大头安是我们大队的人,‘大头安,辘轳脆’要说也是我们自己人说,外人怎能瞎搅和呢?这也太欺负人了!”——白北大队的孩子们大概都是这样想的。就听王帅兵断然喝道:“闭上你们的臭嘴!哪儿来的滚哪儿去!”大家也都纷纷嚷嚷,要他们立即滚回白南老家去。但是,对方似乎不不把这放在眼里,他们不知是因为正在兴头上呢?还是故意挑衅?依然我行我素,高声叫喊着,雄赳赳,气昂昂地就走过来了。这还了得!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嘛!白北大队的小子们立即沆瀣一气,同仇敌忾。王帅兵气势如虹地大喝一声:“打他们狗日的!”双方孩子扭打在了一起......白南的小子们终因寡不敌众,被打得落花流水,屁滚尿流,纷纷抱头鼠窜。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头安应该是幸福、快乐的。他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虽然也是补丁摞补丁,但是,那时候大人孩子有谁的衣服上没有几块补丁呢?也从没见他的娘对他大声呵斥过。他那寡言的母亲下工了,一回到家就很少再路面了,穿针引线、缝补浆洗、一日三餐,放下这个,拿起那个,家务活没有做完的时候。饭做好了,她会叫一声坐在门槛上的大头安:“安——,吃饭啦。”声音也不大,细细软软的,刚好听到的那种,但是,细心的人会听到一种无法言喻的苦涩与寂然。 而村里其他许多孩子有谁不是爹娘的出气筒呢?呵斥、责骂、打屁股就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大人总是心情不好,动不动就要发火儿。可是,又有哪个孩子不是家里的小劳动力呢?能扭扭歪歪走路了,能拎得起篮子了,就得下地干活:打猪草、拾粪、搂末子(用一种专用的竹耙子搂枯枝败叶,集肥用),诸如此类说重不重、说轻也不轻的活计。就拿王帅兵来说吧,他的父亲像个黑面神,不要说王帅兵,就是别的孩子见了他也都吓得退避三舍。他给王帅兵制定下每天的劳动量:隔天,一大荆篮青草,一箩筐粪。完不成,就要挨骂,甚至挨揍,或者不能吃晚饭,究竟是哪一种,就要看他父亲当天心情的好坏了。可是,他父亲好像就没有心情好的时候。这青草还好完成,一箩筐粪,还真是难办。村里就那几头猪,就那几个屁眼儿,拾粪的孩子又多,街上往往光光的根本就拾不到粪。王帅兵就到野外去,他一手拎着粪筐,一手提着粪铲,走得风生水起,野地里、山岭上、丛林里、小河边,沟沟坎坎随便什么地方都去,牛粪、马粪、驴粪、人粪,管它什么粪只要是粪,尽管往筐里撮。急眼的王帅兵常常是看见一抔粪就像见着了一个大元宝。暑假里,中午头儿,大热的天,一个十二三岁的花季少年,四处奔走,为着一抔粪而伤着脑筋。这情景是当今的孩子能理解的吗?王帅兵是有想法的,他要尽快完成任务,下午就可以大玩一场了,父亲的心情再不好,也会理屈词穷,没话可说,没屁可放——他有时非常痛恨他的父亲。但是,他的父亲就容易吗?他们家的成分高:“黑五类”之首地主,在王帅兵的爷爷老地主去世后,一切罪责都落在了王帅兵父亲的头上,除了隔三差五挨批斗,每天还要干生产对里最苦、最重、最累、最脏的活儿,例如:掏生产队茅坑的大粪,出牛栏粪、羊圈粪。可是挣的工分却最少。他哪有心情好的时候?家里又有一堆孩子——男娃女娃五个——那时,一般家庭都是这个数,有的家庭甚至七八个孩子,还有十个以上的。这些孩子,哪一个都要吃饭,都要穿衣。王帅兵父亲的脸整天阴沉得就像狂风暴雨即将来临的天空,他见不得孩子们的是是非非,打打吵吵,胸中的无名邪火腾的一下就会蹿起来,瞬间燃成熊熊大火。他们家锅碗瓢盆生活交响曲常常演奏得热热烈烈,铿铿锵锵,如疾风骤雨。 所以,大头安是快乐幸福的。可是,快乐幸福的大头安却生病了。 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道理?可是,全村人谁也没有想到二十岁上健壮得像一头牛犊子的大头安会生病,并且是那种病,直肠癌,绝症。消息不胫而走,老老少少心里都不好受,大人们唏嘘慨叹:“可怜啊,孤儿寡母的。”随后,大人们的举动给我留下了没齿难忘的印象,至今回想起来心里依然会盈满一种无法言说的令人感动的人间温情,以致我深信不移:不管日子怎样艰辛苦难,人类善良的本性啥时候都不会泯灭。大人们争先恐后地伸出了援助之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很快,一向幸福快乐的大头安幸福地住进了城里的大医院。手术很成功。医生说幸亏发现的早。医生说如果一年后不复发的话,很可能就会没事。 可是,大家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年后,大头安的病复发了,且来势凶猛,医学再也没有回天之术了。 大头安死了,刚满二十一岁。他的母亲用手轻轻地抹下他的眼皮,那双婴儿般清澈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他的母亲给他洗了脸,洗了手,也洗了脚,给他换上了一身儿干干净净的衣服。在邻里们的帮助下做这些的时候,她一直喃喃地说着:“这样也好,这样也好,走在我的前面。”又说:“拖了老少爷们的福,他活着的时候,也没受多大罪。”这个向来沉默寡言的女人,此时,怎么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叮叮淙淙,像小河流水一样不休不歇,“这一年的寿命是老少爷们给他的,他这样的一个人,值了,值了,他是个有福的人啊!”她不停地念叨着,软软的,缓缓的,在场的婶子大娘们听着听着,无不热泪涟涟。 成年的我总认为,大头安的早逝是慈悲的上帝有意的安排。阴晴圆缺,尘世并不完美,实际上有太多的缺憾。尘世的凄风苦雨,风霜刀剑,哪是单纯朴实的大头安所能忍受的?上帝心明如镜,他不忍心啊!于是,大头安在人世上快快乐乐地走了一程之后,他就毫不犹豫地把他收了去——让他继续去过幸福快乐的生活。大头安是专门过幸福快乐的生活的人啊! 大头安去了,“大头安,辘轳脆”的歌谣,随着大头安的离去也永远的销声匿迹了,村落里再也听不到那天真无邪的、嘹亮的、像阳光一样清澈明朗的童音了。可是,那歌谣却永远回荡在了我童年的岁月里,并带着一种类似苦艾的既清香又苦涩的味道。 赞 (散文编辑:可儿) |